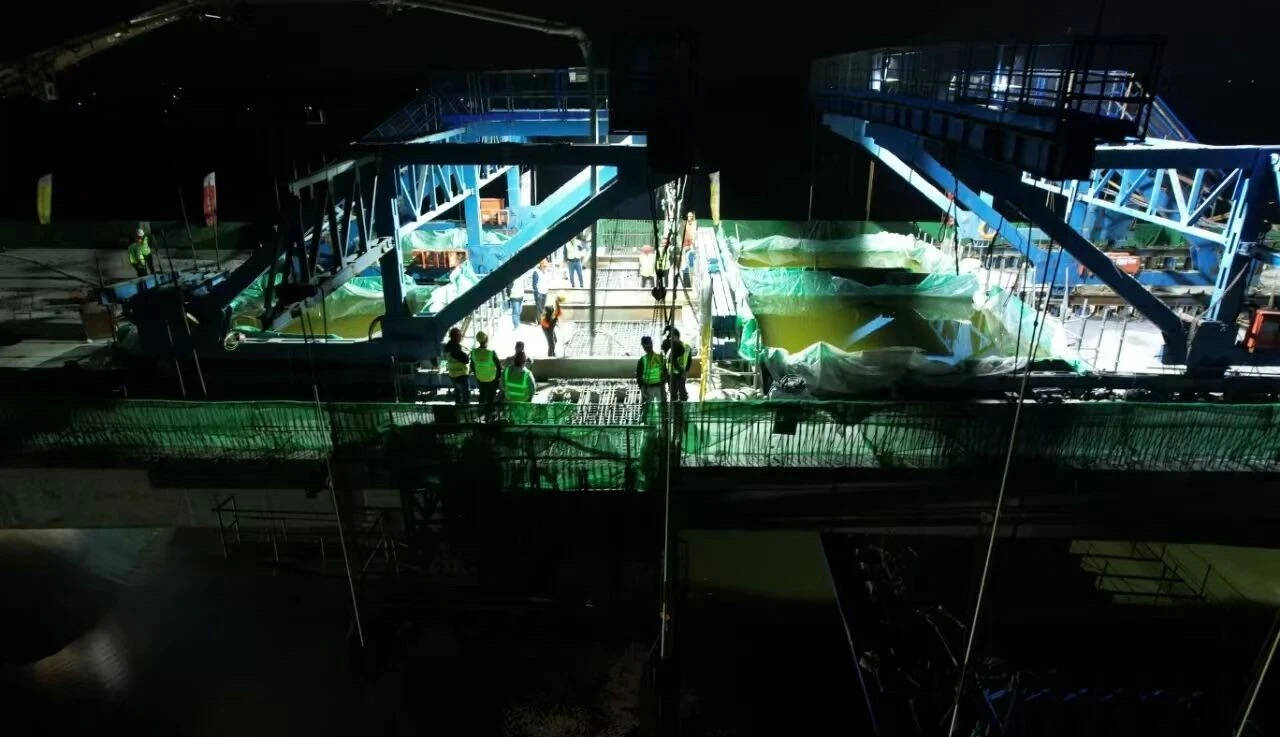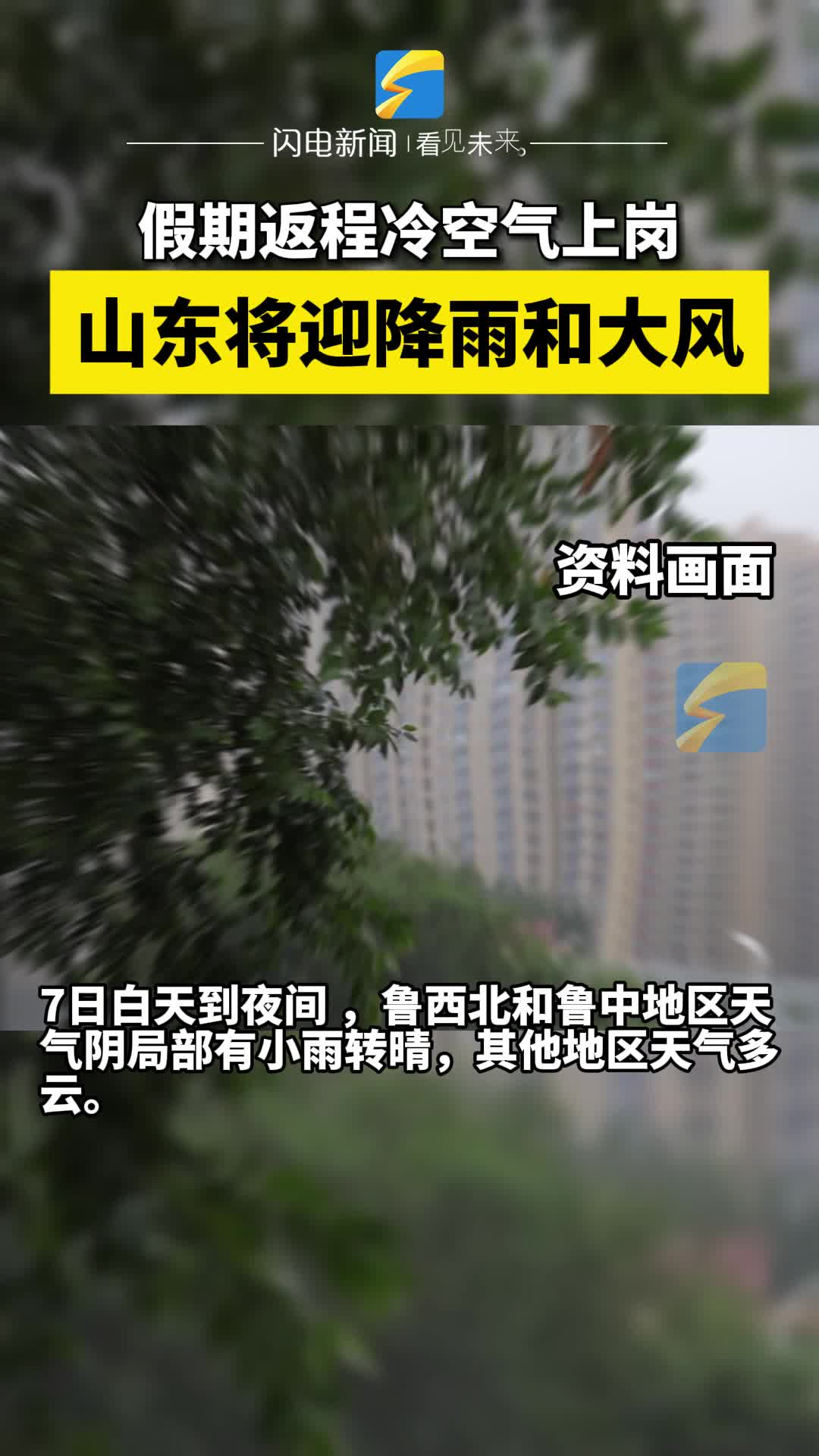作者 王國波
泉城濟南,聞名中外。但“泉城”一詞,并非新中國后始創。“泉城”雅號,也非濟南一城所獨享。1106年之前,即蘇轍創作《遜往泉城獲麥》《泉城田舍》之前,在已見的典籍石刻等文獻中, “泉城”一詞,至少在4個朝代以不同形態出現過,且恰巧都出現在“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上:

一是作為建筑物。公元289年至公元303年間晉代陸機創作的《洛陽記》中,首先出現“泉城”二字:“城外有宣陽觀、千秋、鴻地、泉城、揚威、石樓等觀”。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說: “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百步一樓櫓,屋臺置一鐘,以和漏鼓。”在這里,“觀”應是軍事瞭望塔,一切為了軍事防御的需要。“泉城觀”疑似呼應古洛陽城西北角的金墉城外狄(翟)泉。作為建筑物,理應比文字記載更早。
二是作為地名。公元554年《魏書》中出現了“泉城郡”:“泉城郡:領縣一,戶七十二,新陽。”另有文獻記載:泉城郡,北魏置,屬涼州。當在今甘肅武威地區。隋初廢。
三是作為謚號。公元570年北齊王劉陽亡故,“齊故泉城王墓志之銘”首現“泉城”二字石刻文字。據民國時期在河南安陽豐樂鎮出土的劉陽墓志銘碑記:“齊故特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濟陰郡開國公贈朔肆恒三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尚書右仆射泉城王劉王墓志。”這一詞條最具魅惑,出現了“齊”“濟陰郡”“泉城王”等信息, 而且墓主人劉陽的籍貫是“太安狄那”人。其實“齊”非“齊魯”的“齊”,而是指“北齊”;“太安”也非山東泰安,地理位置約在今山西壽陽北。
四是雅號代指。公元897年唐代黃滔撰寫《泉州開元寺佛殿碑刻記》:“初僕射太原公,以子房之帷幄布泉城,以叔度之袴襦纊泉民,而謂笁乾之道與尼聃鼎。”

此外,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在雍正朱批諭旨《奏明郡城垣事》中也出現了“泉城”:“每遇大雨後勘閲聚水處所平地水高數尺因查泉城歷年受水……伏思泉州一城關系閩南門戶似應早為修葺”。可見,唐、宋、元、明、清,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泉城”“泉州”交替出現在官方、民間的各種記載中。
黃滔用“泉城”代指泉州,比蘇轍用“泉城”代指濟南早了209年。雖然蘇轍將《遜往泉城獲麥》《泉城田舍》親自輯錄在《欒城集》,但因蘇轍晚年受到朝廷排擠,“三蘇”作品被毀版禁刻,致使蘇轍用“泉城”代指濟南在當時知之甚少,沒有迅速傳播開來。
濟南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失去信心。蘇轍親自輯錄的《欒城集》后被明《永樂大典》、清《四庫全書》全文收錄,永存史冊。雖然一般人難以窺見《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但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商務印書館相繼出版發行了王云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國學基本叢書》,蘇轍的十卷本《欒城集》均被收錄其中,《遜往泉城獲麥》《泉城田舍》收錄在第八卷。據報道,為收藏王云五主編的這兩套叢書,全國新增近三千個圖書館,其閱讀量、影響力不言而喻。
尤為令人震撼的是,濟南解放為泉城新生提供了爆款平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陳毅元帥的詩作《泉城活捉王耀武》,以及眾多的南下干部在軍旅詩作和行軍日記中,都對泉城濟南贊不絕口,在大江南北為濟南徹底叫響了“泉城”這一城市品牌,這就很好回答了為什么在解放后“泉城”雅號如此迅速聲名遠揚、如此程度深入人心。
2022年6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四川省眉山市三蘇祠時指出,一滴水可以見太陽,一個三蘇祠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們說要堅定文化自信,中國有“三蘇”,這就是一個重要例證。濟南可以順勢而為,借助超然樓的火爆,講好蘇氏兄弟情系泉城故事;還可以借助陳毅元帥親筆題字的解放閣,續寫“濟南解放泉城新生”的動人篇章。
除福建泉州外,目前河北邢臺、貴州烏當等多個城市、景區,也都在借助文旅融合,闡釋當地“泉城”淵源,講好當地“泉城”故事。